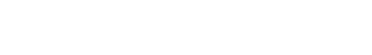工作就是面对一具具尸体
穿过医学院校的解剖楼长长的走廊,福尔马林苯酚类等气体扑面而来,从实验准备室打开的门往里面望进去:橘红色的布覆盖着一具具尸体,解剖实验员正在细致地做着一件件标本。
为保证学生们直观地学习解剖,人体解剖学系的实验员需制作大量的解剖教学标本,常常要加班工作。“这些日子简直可以说是不分昼夜,No Saturday,No Sunday,Just work,work,work,差不多吃住都在解剖楼了啊!”刚刚参与工作近八个多月的毛志远说。
於平老师从事解剖实验员工作已近30年,长期在一线工作的他,如今依然准时往返于江宁校区和汉中路的家中(两地相距近30公里),曾因工作繁忙,过度劳累致视网膜炎。
“从宿迁回来,凌晨3点才到家,早上8点半准时到班开始一天的工作。”庄晓俊是南医大的解剖实验员,也是市红十字会的遗体接收员,这两项工作填满了他的生活。这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工作,他需要不时地面对失去生命的身体。不管遗体捐献志愿者去世在节假日或是在深夜,家庭住址是远离学校,还是偏僻难寻,负责遗体接收工作的解剖学教研室老师们总是不辞辛苦、牺牲休息时间将遗体接收到学校。
不敢告诉妻子自己的工作
庄老师在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却不敢告诉妻子,自己在从事遗体接收工作,只说自己是教研室里的实验员。“有工作上的不开心,不愿对自己的妻子说,因为她已经付出很多了。每天承受的许多委屈,也只能自己往肚里吞咽。”
而刚刚成为解剖实验员的毛志远却很幸福。在多宝·体育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实习的女朋友,每周末有空就会从下关到江宁校区解剖楼(两地相距近40公里)看望毛志远,全力支持着男友的工作。
不过,解剖学系还有实验员的家庭问题还没有着落。然而,他们的困扰远不止这些。“五个人掌握着全校七千多人的医学基础教学。”人体解剖学是生物医学的基础,是每一个医护人员必修科目。目前临床诊疗中还存在一定的误诊率,也有赖于病理解剖分析病因、改进医疗、发展科学。医学教学或科研离不开解剖标本。然而,全国各医学院校都存在这样的问题——解剖实验员紧缺:有学历的,不甘心做这样辛苦而基础的工作;有经验的,学历又欠缺。现在迫切需要既有学历,又有经验的解剖实验员,他们不仅仅是做标本、实验准备工作的实验员,同时应成为学生实验课的带教老师。
前辈经历激励后人
首创《连续层次法解剖图谱》,多宝·体育原解剖教研组主任、基础部主任姜同喻教授,在他研究解剖学的年代,还没有遗体捐献,只能在刑场、野地里找到遗体,把它背回工作室。那本至今仍被人体解剖学界认为经典的图谱,就出自于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工作室。姜同喻教授2007年不幸因肺癌去世。“老先生身体一直挺硬朗,如果不是由于长期受福尔马林苯酚类等有毒气体的伤害,会在这个世上活得更久。”
遗体接收员与解剖实验员做的一切,是在为一个个神圣的生命让道。
南医大校园记者 姜海婷
本报记者 耿莲莲